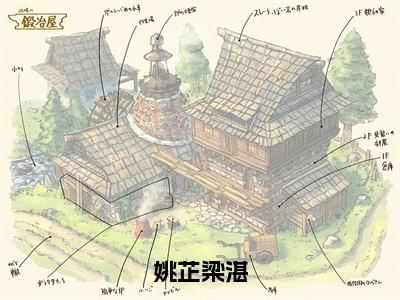短文地下大佬的女人张宗延乔烟免费阅读-地下大佬的女人张宗延乔烟无弹窗
|
脚踩在悬崖,鱼龙混杂的东莞是最后的退路。那边大小酒吧发廊足疗比比皆是,咱去了花点钱,有窝藏点,更重要是东莞毗邻深圳码头,逮着良机,我们可以偷渡云南,金三角老Q捣了您的老巢,地界大了,您的余党在,切割山头不是没翻盘的可能。张三爷的名号,各国毒枭都认。M 我准备好枪,将窗帘一扬,霎时黯淡的房间灯火通明,擦枪走火的动静炸裂在咫尺之遥的屋檐,震得房顶晃三晃。 东完的小足疗店,躲几天,取迟_周,红桃联络你们,她在东莞市区有房子,宾馆和店铺不保险,逃脱条子的绞杀,越是繁华热闹地段越占尽先机。僻静反而目标清晰,挨着菜市场和商业街,你们容易混迹。红桃绝不出卖。" 隐隐约约的,窗外劝降的嘶吼减弱,被一道更为气势磅礴的类似推土的声响覆盖,我嗅到了浓重的火药味,这味道我太熟悉,军区专用爆破,不会造成死亡的土性炸弹,凡是不足二十米高度的楼盘,瞄准极其精确,某一层、某一间、最小范围十米左右,半斤的炮仗,轰得定位一滩粉末。 毕竟属于杀伤力武器,区军部使用务必上报,批示流程三到五日,而省军区下至副团干部当即调用,我基本断定,来者是东三省的少将以上军衔。 如此大费周章,恐怕不毙掉张宗延,也得扒他层皮了。 我情急之下推搡他,〃快走!我有法子周旋拖延。" 张宗延解开束在腹部的绳索,牢牢地扼住我,"小五,你不是曾经的你了。" 我一瞬间呆滞,迷茫跌入他眼底猩红的漩涡。 我忘了。 我不再是昔年的乔烟。 我何尝不是法律操纵的是非中恶贯满盈的土匪。 我决意跟随逃犯亡命天涯的一刻,就回不去了。 我洗不掉血,洗不掉罪孽,洗不掉历史。 我与张宗延都是世俗道义不容的人。 我无力伏在他肩膀,像缺失了氧气的鱼,游荡在风月大梦荒唐。 "许多人说我聪慧,生来是当官太太的命,襄助丈夫,辅佐仕途,张老板现在还觉得我聪慧吗。〃 有两滴雨,温热的雨,滑落在额头,鼻梁,湮没我的唇。 腥咸,苦涩,滚烫。 他声音是无边无际的钝痛,是枪林弹雨不舍,又不得不舍的沙哑和死寂。 "是我的错。〃 他仰起头,破败的房梁满目疮癀,遍布着炮火洗礼后的焦黑,“我护不住你,不该抢你。 "我没有恨过你。" 我注视地面交缠的影,“我坏透了,骗你这样久。" 我记得米兰说,红尘里的姑娘,恨一个人,比爱简单。 卑贱的泥土,浇灌出的皆是恨与苦的鲜 花。 爱何等难以企及。 情字当头,悬而未决,手起刀落,总比不肯自我放过的恨,畅快得多。 我埋在他胸口贪婪吮吸着,想把他的气息一点不剩的刻入骨骼里,“等我去找你。"又是一声枪炮,在九天云霄泛滥,张宗延苍白的五指捧起我的脸,抵死缠绵的吻着,我听到他困兽般的闷吼,在喉咙翻滚,我也听见自己的呜咽。 我并非不畏惧死神。 我时常想,我究竟拥有过好日子吗。 看似衣食无忧的岁月,它包裹着我曰夜不安、捍卫与掠夺的尔虞我诈,惊心动魄。 我不敢输。 上苍不绐我二度重来的机会。 踏实的时光,寥寥无几。 世人得不到钱财,我得不到安宁。 我也不是真的快乐。 这个忘乎所以,向生死宣战的深吻,毁灭了我和张宗延胸腔内积存的每一寸呼吸,枪声所过之地,愈发清晰,秃头明白来不及了,弯腰奋力撕扯张宗延,他握着拳,眸子里满是狰狞的血丝,在秃头的哀求拖拉下拽出了房门。 第229章你要我死是吗 (中) 癫痫。 我屈膝跪在堆满碎玻璃的毛毯,背部紧贴墙壁,默数着时间,一秒,两秒,五秒, 十秒。 当我数到第四十七下,一辆罩了防弹铁皮的越野车呈万夫莫开之势从酒店的地下车库斜坡飞驰而上,快似闪电,撞得特战兵措手不及,第一排被掀翻,第二排死撑着爬起,一通凶残的毫无章法的扫射,铁皮在密集的攻击中,焚烧一簇簇火苗,电光火石间, 油箱幵始漏油。 我有条不紊在脑顶罩了一支礼帽,遮住命门即眉心,强迫自己镇定,一名追得最猛的特战兵险些爆破了左后的轮胎,假设得手张宗延插翅难逃。 我不再观望,而是持枪对准特战兵的大壳帽边缘,发射了一枚金色尖头子弹。 子弹的威力极强,奈何我枪法不精,差了一厘米,他的帽子被击飞,皮囊毫发无损,整个人踉跄匍匐。 我无心恋战,护送张宗延逃出生天才是当务之急,我接连打空了弹匣,绊倒一排穷追不舍的特战兵,他们大多轻伤,有一人攀上了越野车的后备箱,试图击碎玻璃偷袭,被我一枪穿透臀骨,折了大胯。 “房间有枪手! 指挥官大喝一声,在越野车破墙消失众人视线后,枪口齐刷刷端向了我。 吧嗒两声,空空如也的干响。 子弹用光了。 条子攻克在即,我没了退路。 我不擅武力,与其和男人缠斗不如缴 械。 张宗延教我射击,未教我蛮力博弈。我捏着空了的勃朗宁,按捺住不由自主的颤抖,缓缓起身,从容不迫立在大军过境的窗前。 底下持枪瞄准的特战兵认得我,大惊失色,"糟糕!禀报参谋长,是夫人!" 硝烟四起的巷子,倒映在我曈孔,倏而_缩 果然是他。 我和关彦庭互相暗算,彼此过招,演绎了一场场精彩的谍中谍戏码,各有输赢,他终归占据上风。 我玩不过他。 他的城府深不可测,最可怕之人,在于透过他的眼睛,也看不到一丝真实。 特战兵举着喇叭,在杳无人烟的空场朝我大喊,"夫人,参谋长跨境解救您,您下来吧,, 解救我。 我不动声色捏住窗台漏发的一枚子弹, 塞进枪膛,按下扳机,插入腰间的口袋。 我和张宗延偷渡的当晚,关彦庭发布声名,关太太遭逃犯张秉南挟持绑架,作为人质押解离境。 他或许不只为声誉,更为关键时刻捞我—把。 主动与受制,是截然相反的概念。 前者让我牢狱大灾,刑场毙命,后者让我洗脱嫌疑,平安无恙。 关彦庭分明愿意救我,为何不能放他呢。 我捆着绳索,自三楼顺延而下,扎实落地,一步步靠近蛰伏的吉普,它纹丝不动,候在那里,像是料准了我们有此一见。 我隔着布料触摸枪械,它还保留方才一 战的炙热。 车门焊死,车窗悄无声息降落,关彦庭笔直端坐在车里,他半副轮廓陷入昏暗的光影中,没有穿军装,只是一件普通的深色系西装,他目视前方,似乎在压抑着怒火。 我停泊在车门之外半米处,"彦庭,张宗延跑了,他去哪里,我不会告诉你。你若想泄恨,大可杀我解气,我只求你,让我自行解决,我不要任何人决断我的生死 |